作者:[瑞典]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没能如期颁布。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以来被视作全球最高级别的文学奖项,作为其评选机构,瑞典文学院在世界文学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8年到2019年曝光的一连串丑闻,却令成立200余年、一直保持着神秘色彩的瑞典文学院跌下“神坛”。
丑闻的中心是一个名叫让-克洛德·阿尔诺的法国人。阿尔诺和他的诗人妻子、瑞典文学院院士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共同经营着斯德哥尔摩最有声望的文化沙龙“论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院士、艺术界名流都是“论坛”的常客。
20多年来,阿尔诺的轻浮好色是人尽皆知的——包括他的那些院士朋友,但人们似乎将其解读为他的法式风情的一部分。阿尔诺用恐惧和羞耻制造沉默,这种沉默又进一步使受害者和知情人相信,他围绕“论坛”和瑞典文学院建立起的人脉足以使发声者付出惨重代价。直到古斯塔夫松的调查揭开尘封的盖子,受害者不再沉默,人们才终于发现,阿尔诺的“轻浮”行为早已达到犯罪的程度。
丑闻不断发酵,弗罗斯滕松利用职务之便影响瑞典文学院奖项评选和资金发放的嫌疑也浮出水面。院士们对于如何应对丑闻持两极化的态度,保守派与改革派爆发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瑞典文学院面临瓦解的危机……
《诺贝尔文学奖消失之日》详细记录了这一系列丑闻曝光的过程,并由此暴露出瑞典文学院内部乃至整个瑞典文化界的诸多弊病。

《诺贝尔文学奖消失之日》,[瑞典]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 著,沈贇璐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论坛”
2009年6月,我第一次听说让克洛德·阿尔诺和“论坛”。那是一个温暖的下午,在马尔默的莫乐坊广场。我在新港餐厅的阳光露台上,对面坐着拉斯穆斯,我和他是在为学生杂志撰稿时结识的。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阅读各种伟大的经典作品,这让我很羡慕。大约在我中断本科的B类课程学习时,他搬到了斯德哥尔摩,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现在他正在马尔默短期出差。
坐在新港的露天台上,光线很明亮,他向我介绍了大学的情况,还介绍了一个叫瓦尔堡的郊区,以及“论坛”的情况。
他问我是否知道“论坛”?我摇了摇头。他说,斯德哥尔摩最好的文化场所位于一个地下室里,由受人尊敬的诗人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和她的法国丈夫让克洛德·阿尔诺经营。拉斯穆斯已经在那里工作了6个月。
他异常严肃地告诉我,他第一次来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感觉很不好。他经常漫无目的地乘坐地铁,作为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有一次他在一个叫奥登广场的车站下车,在扶梯上他突然认出了他大学里的一位男性教授。他向教授打招呼,在他们简短的交谈中,他提到自己刚来这地方。那位教授于是提出,他很愿意把拉斯穆斯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让克洛德·阿尔诺。教授说,“论坛”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很快拉斯穆斯就开始在“论坛”打义工,他负责在演出后打扫地下室。
当我在近十年后的2018年春天再次回想起新港的时候,很多故事都记不得了。
我记得我没有戴太阳镜,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当时我刚从抑郁症中恢复过来,走出长时间呆在公寓里的状态,我开始回到现实中来,所以对自己的强烈反应感到兴奋。我仍然记得那次谈话对我情绪的影响。但拉斯穆斯那次到底告诉了我什么?他现在还记得吗?我通过Skype询问了他。我们现在仍然是朋友,尽管已经有几年没说过话了。他现在正在美国攻读文学博士学位。
拉斯穆斯
我记得,“论坛”曾是我梦想的全部。所有重要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都会去那个地下室活动。每个人都是我从初中阶段就崇拜的对象。只要走下楼梯,看到一群文化名人,就是一种“伟大的经历”,这是我读过的书中的景象。世纪之交那一批的小说中,常常描写主人公搬到了首都,突然被扔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然后叙述之后的故事。他们在那里就仿佛受到了持续的冲击。就像《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第一次去参加舞会时:她极其留心富人的举止和他们使用的语言。她还很留心他们的美,与年轻无关的美。这种场合使她的感官更加敏锐。在地下室里,我还记得文化部长结束与萨拉·达尼乌斯的谈话,转而与霍拉斯·恩达尔交谈的五秒钟。“论坛”是一个让你获得经验的地方,感觉上很文学。这种经历是如此重要,有一天你可能会亲笔写下这段往事。
当我完成清洁工作后,我被允许来到瓦萨霍夫,那是参与人员和圈子核心人物用来消遣夜晚的酒吧。核心人物通常是让克洛德、霍拉斯·恩达尔或瑞典文学院的其他院士,会请几个音乐家,或是一个戏剧演员,有时甚至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自己也会来。我和让克洛德的年轻女助手们坐在聚会的边上,这些助手被称为姑娘们。我有一种感觉,他可以公开地、不被反对地触摸她们。不过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情形了。会不会我其实根本没见过这情况?我的经历是否源于让克洛德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萨德侯爵的行为,或是我自己感到不适,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感觉呢?我不知道。我是唯一一个为他工作的男性。他经常谈到说我很被动。他说,如果我有一天成功了,那要感谢他和这个“圈子”。他经常把“论坛”描述成一种家庭般的存在,因为人不会抛弃家。
去过瓦萨霍夫的晚上,我能记得,我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但是,当我之后乘坐地铁回到郊区时,我仍然会强烈地涌起一种冲动,我想给别人打电话,告诉他们,说我刚刚和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葡萄酒。
我在“论坛”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有个年轻女孩开始常来听那儿的古典音乐会。她总是一个人来。她长得很漂亮,也像我一样害羞。这让我立刻为她担心起来。
就好像我和让克洛德待了这么久,我已经能把握准他的目光。因此,在她出现了几次后,我甚至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猜到,他会在休息时间找她。他走过去,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她看起来很惊讶。他又低声说了几句,她就起身跟着他进了办公室。中场休息结束,下一首曲子开始演奏时,他就回来了。但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也许我们在马尔默见面时,我告诉过你这件事情。也许我没有。也许我当时只是说,让克洛德身边围绕着很多女孩。但我已经开始感觉到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使我和你在聊“论坛”的时候会加以粉饰。同时,我也希望你能明白,我曾经也是那个圈子的一员。
那晚,当拉斯穆斯和我在马尔默分道扬镳时,天气越来越冷。我对他的故事的某些部分感到好笑,并说这听起来像是对认为所有成功人士彼此都是朋友的那种想法的戏仿。但他描述的地下室是真实存在的,它证实了我对文化界的印象,它确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一个住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大公寓里的人的圈子,那里的楼梯间像教堂一样凉爽和宽敞。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十几岁时想进入这个世界的原因。伴随我长大的基督教会,常常谈论一些最宏大的问题和最宏大的答案。他们相信永恒的生命,在那个时代的视角下,我可以体验到一种被选择的感觉——一种不受当下摆布的安慰和解放的感觉,可以不用被抛弃、不用被扔到当下的感觉。而当我开始对此产生怀疑时,文化作为一种可能的出路出现在我眼前。它成为唯一能衡量我所离开的环境的东西。
我发现,小说和音乐是社会的另一种例外:那是一个允许各种黑暗禁忌的思想存在的空间。我想,那些能把自己的经历转化为艺术的人,一定也会产生被保护的感觉——一种对于比自身更大的东西的归属感。但最重要的是,我对写作的人和文化世界本身有一种浪漫的看法。我想象着,一旦我被允许进入这个世界,那这里也就变成了自由地带。
在我早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写到我对瑞典剧院中关于饮酒和性骚扰的辩论感到多么的失望和无聊。我无法忍受自己听到斯德哥尔摩的大演员们否认这种混乱的局面,并立下保证,说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在5点下班回家,他们“都是在自行车后座架上放着一个儿童座椅的普通父母”。
在2009年的夏天,我知道焦虑往往是写作的阻碍,但拉斯穆斯的故事让我的那些早期的想象变得鲜活起来——并添加了些许不适。
当我穿过莫乐坊广场时,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写一篇关于斯德哥尔摩的地下室的报道。
这个环境是我本来绝不会靠近的,但这项写作任务开始成为我靠近那个圈子的途径,我想着或许我可以在学生报纸上发表这篇报道,或者我可以尝试把它卖给《瑞典南方人报》。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谈论的可能是性骚扰。我也没有用这一概念。然而,这个故事包含了一种无力感,我甚至可以在身体层面上感受到,这是因为对颓废的地下室的描绘,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我在手机记事应用程序中写下的想法既强烈又模糊,所以当下我没有被触动。但这些想法并没有离开。
文:[瑞典]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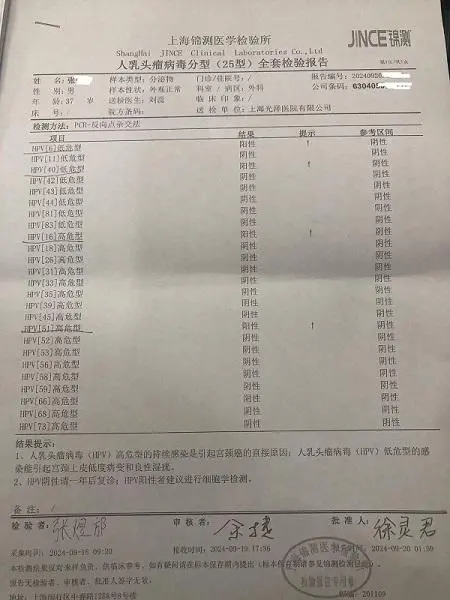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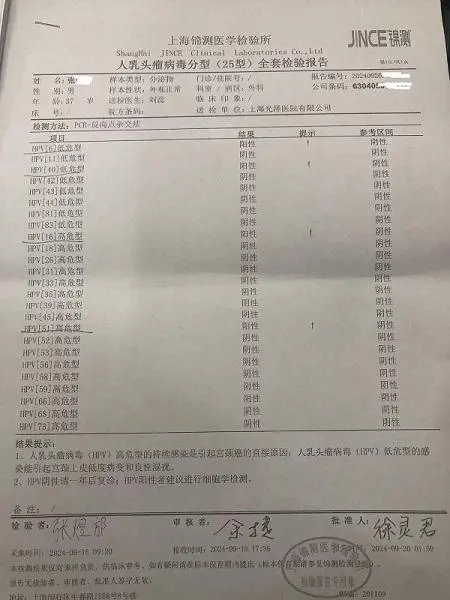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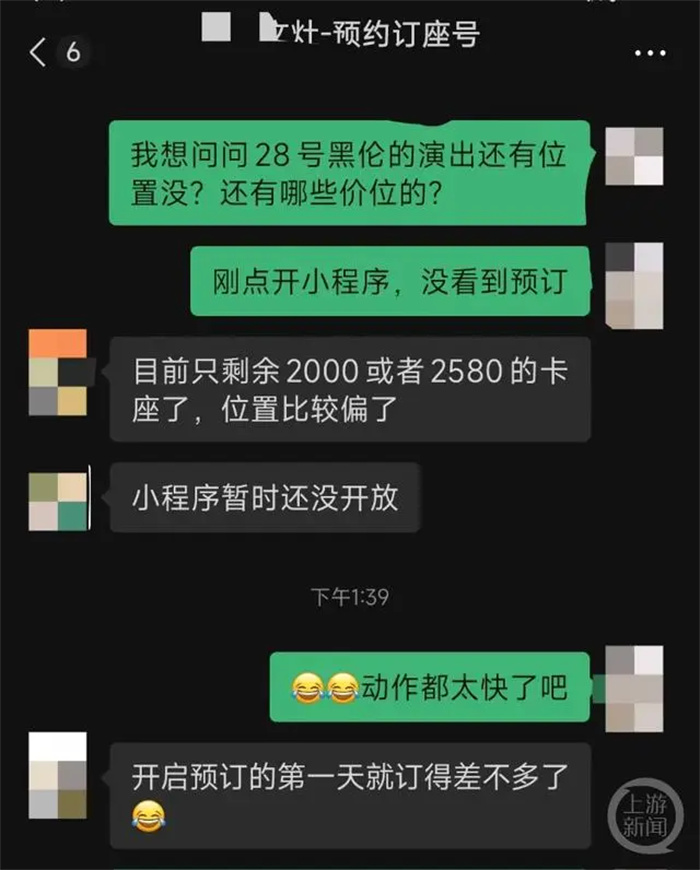






要发表评论,您必须先登录。